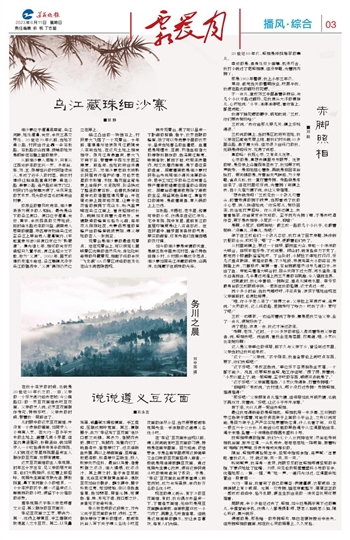■刘毅
20世纪60年代,照相是件挺稀罕的事儿。
幸运的是,虽身处穷乡僻壤,机缘巧合,我打小就过了把照相瘾,但没穿鞋,光着两片脚丫。
那是1963年暑假,我上小学三年级。
某日,做完当天的暑期作业,吃罢午饭,我便在路边的晒场打陀螺。
不一会儿,堂叔刘三手里拿着条麻袋,与几个小伙子路过晒场,见我满头大汗的模样儿,心疼地说:“小子,消停消停吧,看你背上,都湿透啦。”
我停下抽陀螺的鞭子,明知故问:“三叔,你们要去赶场哈?”
三叔说:“去你爸那儿耍几天,镇上好玩得很。”
三叔说的镇上,当时是区政府所在地,我父亲在区邮电支局上班,距我们村也就20多里山路,虽不算太远,但对很少出远门的我,无疑是诗和远方,充满了诱惑。
真的吗?我既心动,又有点儿犹豫。
心动的是,真想去镇里开开眼界。犹豫的呢,是母亲上山摘四季豆去了,我如果不吭声就走,一是怕她担心着急,再就是怕回来后挨打。更关键的是,开春后天气暖和,为少穿鞋,省点儿钱,我一直打着赤脚。走路倒是练出来了,但在村里还好说,光着脚丫到镇上去,自个儿难为情不说,会让父亲难堪。
“想去就走呀!”三叔见我一个劲儿勾着头,盯着赤裸的脚不吱声,当即看透了我的小心思,快人快语地说:“你妈那儿,赶场回来,我给她打声招呼。你从没到过镇上,去看看稀罕,你爸肯定会欢迎的。至于两片光脚丫嘛,不是去吃酒作客,更不是去相亲,小屁孩一个,怕啥?”
是啊,小屁孩,怕哪样哦!跟三叔一路的几个小伙子,也跟着起哄:“没事儿,没事儿,走吧!”
架不住三叔他们一个劲儿忽悠,我打消了回家穿鞋、换件新衣服的念头,咬咬牙,“嗯”了一声,便跟着他们去了。
从村里到镇上,要过一个田坝、翻两座大山、穿越一个深深的大峡谷。田坝平坦好走,不成问题。爬山时,就有些体力不支了,感觉两个膝盖酸溜溜地疼。下台阶时,小腿肚不停地打闪闪,好几次差点跌倒。更难受的是,不少地段,布满鸡蛋大小的碎石,赤脚踏上去,刀割般疼,弯腰一看,右后脚跟居然划开几道口子,渗出了血。穿越马槽滩大峡谷时,因头天刚下过大雨,河水猛涨,滩水汹涌而出,几乎漫过河滩上两三尺高的石跳蹬,令人望而生畏。
过跳礅时,我心中害怕,一脚踩空,差点儿掉进水里。幸亏紧跟身后的三叔眼明手快,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这才逃过一劫。
两个多小时后,当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地出现在父亲面前时,他满脸惊愕。
“哇,你小子怎么来了?”惊愕之余,父亲脸上写满疼爱,连声说:“大热的天,这么远的路,把脚走坏了咋办?吃饭了没?累坏了吧?”
三叔一边喝茶,一边讪笑着说了原委,算是把我交给父亲,坐了一会儿,便赶场去了。
洗了把脸,休息一会,我这才缓过劲来。
“走啊,老刘。”这时,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微笑着走进父亲宿舍,说,照相去吧。说话间,看我坐在角落里,打趣道,哇,小家伙也来赶场啊?
这人是父亲单位的领导,前不久与父亲下乡,曾经到过家里,父亲当时让我叫他韦叔。
“这个……”父亲说,“孩子刚来,我准备带他上街吃点东西,要不,你们去照吧?”
“这不好吧。”韦叔正色说,“单位好不容易拍张全家福,一个都不能少。况且,还要照标准照,贴工作证呢。”愣了愣,接着说:“小家伙碰上了,就一起照嘛,至于吃的东西,顺便买点就是了。”
“这不好吧?”父亲面露难色,“小家伙走得急,打着赤脚哩!”
“怕啥呀?”韦叔说,“农村娃儿,哪个没打过赤脚?赤脚照相,难得难得!”
“那好吧!”父亲颇有点儿难为情,但领导如此开明热情,也就不再反对,笑着说:“好吧,让这小子开开洋荤。”
接下来,大伙儿便一起出去照相。
最让我觉得新奇的是照相机。照相机用一米多高、三只脚的枣红色架子撑着,可能安装在架子上面的小平台上,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架子上严严实实地蒙着块红绸,什么也看不到。只见一根五六十公分长、比电话线还粗的黑色绳子从红绸里钻出来,绳子末端,坠着一个深褐色的椭圆形塑料小球。
按照相师傅的指挥,我们六七个人分两排站定,然后他走到相机后面,掀开红绸,一头扎进去,窸窸窣窣地一阵鼓捣,接着听到“啪啪”两声响,好像开箱或关箱似的。
随后,照相师傅抬起左手,竖起中指和食指,连声喊:“注意啦,看我这儿。对,就这样,笑一笑,笑一笑。”
听到喊声,我浑身一激灵,两眼紧紧盯住照相师傅竖起的手指,下意识地扯了扯嘴。少顷,只见他扬起握着塑料小球的右手,优雅地那么一挥,一捏,“嘭”地一声,一道闪光划过,红绸里倏地冒出一股青烟……
大约一周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尊容:表情僵硬,衣服破旧,左侧裤腿上有个破洞。尤其一双赤脚,插在穿戴整齐、周周正正的一帮叔叔伯伯中,格外扎眼,硬生生挤出来的一缕笑容比哭还要难看。
晃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照相,如今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手握智能手机,仿佛人人都是摄影师,想怎么拍就怎么拍,随心所欲,高兴就好。
遗憾的是,那张唯一的赤脚照片,早已在辗转搬迁中丢失。但赤脚照相的画面,却在我心灵的屏幕上,久久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