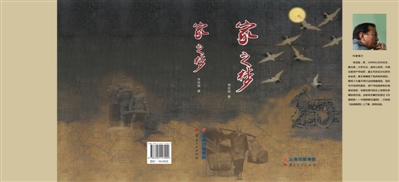这不仅仅是太平这个山沟子给他带来了兴太和兴平一双儿子,而是太平这个地方让他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他感到,他这一生中,在太平的这三年,也仅仅是这三年,尽管国家发生了天大的变化,尽管无数的人都死于这人祸加天灾的不幸之中,而对于他,却是最安稳的三年,最没有思想压力,心里倍感轻快的三年。
他进一步回顾自己走过的45年人生历程,无论是当学徒,在部队,在军校,在战场,还是受伤后到地方这些年;也无论是在国民党政府还是解放后在共产党政府,他一直是遵纪守法,秉持严格的做人标准,更不曾听信那些对共产党怀恨在心之人的蛊惑,去干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之事。尤其是解放以后,他自认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思想上是一致的,从行动上是支持和真诚拥护的。
即便看到有些政策和做法明显存在失误,甚至预感到将会引出大问题,他还是顾大局,讲方法,从来不在群众中散布谣言,指桑骂槐。总而言之,在他已经走过的这短暂的一生中,没有丝毫愧对祖宗先人,愧对当局政府,愧对百姓父老的地方。
黎慧智来到太平以后,新结识了诸如吴光符、李松涛、杨峥珖、兴犁的养父邹成明以及黄志恩先前曾相处过的黎耀齐和付永刚等朋友,并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虽然各有差异,但内涵一致的山里汉子的人性和人格之美。这些看是一个个山夫粗人,但却是正派厚道,情深意切,肝胆相照的乡邻挚友。此时,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正一个个在他脑际不停地闪现。
继而联想到自己负伤后,在宋光生和廖长武的不离不弃之下,从广西南丹,一路经独山、都匀到贵阳图云关获得救治;在高坪养伤期间结识并成全了他和黄志恩喜结良缘的汪医官,以及吴家坝那位心地善良的陈幺嫂;再辗转17临教院生活了近四年;所到之处,看到并接触了大量的农夫山民、少数民族兄弟和那些曾经英勇杀敌的荣军将士们;这些普通民众的豁达开朗,彪悍勇猛,诚实以待,甚至是舍生取义的高尚品格,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从中受益颇多,因此经久不忘,永世不忘。
每当黎慧智站在高处,尤其是站在伍家垭口或毛栗坡上,看到太平这山窝子里从山野四处毫无规律地缓慢升腾的东一缕、西一缕似乎有些孤独的炊烟,总会联想到他的家乡,那远在北方大平原上,从一个又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里,随着风向,升起的颇有阵势,密密匝匝的另一种态势的炊烟。他能看懂这两者之间,自有它惯俗的规律和不同寻常的韵味。前者飘逸时间短,显出小家碧玉般的轻盈飘渺,简朴平淡,各持风姿,往往伴之以山间的雾霭一道升腾,更依依不舍对大山的眷恋,最后形成那紧紧缠绕在山腰的美丽山岚再也不肯离去。后者飘逸时间长,显得密实敦厚,相互渗透,结伴而行,往往你追我赶,互为依托,共同去追寻那天边的祥云,为蓝天点缀出绚丽的斑斓。
如梦似幻的炊烟,是北方平原的点缀,是太平山乡的缩写,是家园的象征,是母亲的憧憬,是涌动激情的酒,是书写豪迈的诗,是火舌在灶膛里跳跃的场景,是浪花在激流中奔放的图画,更是黎慧智深藏在心底的对家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家”的一世祈望。
遥望炊烟,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在灶房间,刚刚吹旺一膛红红燃烧的柴草。
遥望炊烟,仿佛又看到父亲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搂着孙子,正从那数千里之外,朝着自己缓缓走来的身影。
遥望炊烟,仿佛又看到或者是故乡的父老乡亲,或者是太平的兄弟姊妹,或正在麦场上打麦,或正在秧田里唱插秧。
遥望炊烟,仿佛正看见黄志恩那一双炯炯的眼神,正目不转睛地祈望他尽快安全地走下毛栗坡,走到她和孩子们身边……。
当看到从麦土湾那幢小木屋的茅草顶上升腾的一缕炊烟时,黎慧智的心扉更是不能平静。因为这缕炊烟,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了却了自己决心要为弟弟成家立业的夙愿。如今,被下放回农村的黎慧真已经与被安置在麦土湾生产队的原太平寺那位还俗居士仇登轮结为连理了。那缕炊烟正是升腾而起的,弟弟的家的标志。
比黎慧真小6岁,时年33岁的仇登轮落户继光大队麦土湾生产队后,在队里社员们的帮助下,从山上砍回几棵杉木树,割回几捆丝茅草,连同砍树时剥下来的杉木皮,凑合着盖起了两小间简易房子。一间作为她的住室,另一间养了一头小牛,生活算是暂时安稳下来。
麦土湾位于小白岩以下几十公尺,距离太平寺大约最多里把路,站在太平寺的院坝内,既可以看得见麦土湾几家农户院子里人的活动,也可以不用很大声音就把人喊答应。
还是在大食堂吃饭时,仇登轮就非常喜欢与黄志恩来往。她佩服这位黄大姐,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年纪,也照样一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带着几个孩子走南闯北,还听说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独自一人居然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165)